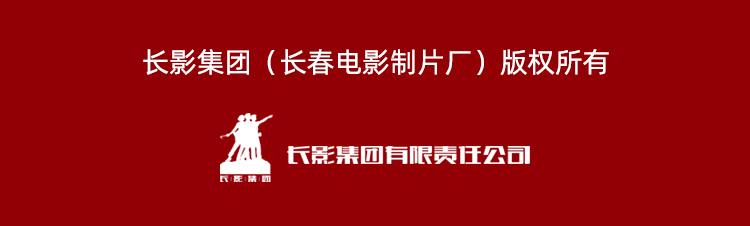[摘要]近年来,中国重工业科幻大片的崛起使科幻电影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市场和影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其背后的文化逻辑、艺术特色与社会意义亟须深入探讨。2024年11月,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和高校科幻联盟联合主办的“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空间想象与故土回望:科幻电影中的空间寓言与故土叙事”在北京大学举办。与会专家深入探讨了科幻电影的寓言式批评、空间建构的象征意义、社会指涉及中国科幻电影中的乡愁情结、土地时空隐喻和科玄之辩等议题。此次沙龙不仅拓展了中国科幻电影研究的新视野,也促进了高校间科幻主题的交流,为产教融合与产学研协同开辟了新的空间。
[关键词]科幻电影;“批评家周末”;寓言式批评;空间想象;乡愁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航天科技等前沿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电影生产工业体系和影视基地设施的不断完善,中国科幻电影产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以《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为代表的作品受到广泛关注与热捧,《疯狂的外星人》《独行月球》《宇宙探索编辑部》《从21世纪安全撤离》等影片也展现出了高水准,赢得了亮眼票房与良好口碑。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科幻电影以其独特的叙事艺术、技术逻辑、视听空间建构方式和文化价值观,为世界科幻电影的多元发展贡献了新的力量。同时,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也得到了国家管理层面的关注和支持,被视为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新动能。随着“科幻元年”的呼声渐起,科幻创作和产业受到广泛瞩目,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也逐渐成型,成为中国语境下文化研究与电影文化批评的重要延伸与创新实践。在此多元语境下,2024年11月13日,第72期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红三楼成功举办。活动以“空间想象与故土回望:科幻电影中的空间寓言与故土叙事”为主题,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科幻迷及北大师生的热情参与。此次文艺沙龙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高校科幻联盟主办,《电影文学》杂志社予以独家学术支持。会议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19级博士生薛精华和2021级博士生刘婉瑶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媒体实验中心主任邱章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高校科幻联盟副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曲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庄维嘉副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访问学者邵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杜天笑等专家学者作为研讨嘉宾与会。
一、科幻电影的寓言式解读:理论、空间与历史
薛精华以《假定性空间中的现实指涉:从冷战到数字时代的科幻寓言》为主题,从理论到实践多维度剖析了科幻电影的寓言性在空间建构、历史进程中的体现及其社会关切,与会学者针对此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寓言式意识形态批评方法阐释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寓言“以另一种方式说话”或“通过间接方式表达”的本质为理解科幻电影中隐藏的深层意义提供了线索。薛精华对寓言概念的阐释揭示了其在科幻电影研究中的潜在价值。她通过援引詹姆逊的观点认为,寓言的表面故事往往隐藏着深层次的、需要被解读的隐秘意义,其核心在于从思想观念角度对故事进行重新构建,例如在经典科幻电影中,看似简单的外星入侵情节可能隐喻着人类对未知的恐惧或对社会变革的担忧。本雅明对象征和寓言的区分是重要的理论突破。薛精华阐述了本雅明对象征和寓言的研究成果,即象征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寓言则因其破碎性、孤立性以及文字与理念的断裂性,展现出模糊性与多义性。她认为,本雅明通过考察巴黎拱廊街的都市空间,揭示了寓言如何反映社会的矛盾性与破碎性化特征。例如拱廊街繁华外表下的小偷、游荡者,以及易碎的玻璃等不稳定因素,象征着商品拜物教和梦幻意识形态背后的深层危机。这一视角为解读科幻电影中类似场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例。詹姆逊的民族寓言批评拓展了寓言的应用范围。薛精华提到,詹姆逊以鲁迅的作品为例说明第三世界文学中的寓言如何投射社会意义。她通过对电影《第九区》的分析认为,科幻电影想象中的人类与外星族群的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科幻设定,还可以被解读为对现实中种族隔离、歧视等问题的反思。这种民族寓言的思维方式为理解科幻电影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电影如何通过外星种族关系隐喻现实中的种族与文化冲突。周志强的“寓言论批评”从现代社会的本质出发指出了社会与现实之间的寓言性关系。薛精华通过剖析周志强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中拜物教文化对现实的扭曲,使得科幻电影成为反映这种扭曲的重要窗口,例如一些科幻电影对未来城市的描绘充满高科技元素的同时也暗示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人性的异化,而这正是寓言用外部意义“拯救”内部意义的体现。陈旭光的“电影寓言式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明确了影视艺术与现实的寓言式关系,他认为“影视艺术与现实之间所构成的关系是一种寓言式的关系而非镜子或照相机式的关系……而是一种以一对多,以形式或结构的有限性对寓言的无限性”。了解电影与现实之间的“互本文关系”,探究电影如何能动的反映社会文化语境,呈现出社会的整体性真实。以寓言的方式批评电影,意味着不再致力于为电影寻找其所对应的精确的所指对象,而是承认电影文本的内涵与外延具有多重的、不固定的,甚至是任意的指向。薛精华同样参考了陈旭光的“电影寓言式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即影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镜像或照相机式再现,而是一种寓言式的关联。在薛精华看来,影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一对多、以形式或结构的有限性对寓言的无限性。也就是说,寓言式意识形态批评的任务在于探究电影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电影与现实之间的“互文本关系”,并分析电影如何能动地反映社会文化语境,既呈现社会整体性的真实,又对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寓言式的批评视角,不再试图为电影文本寻找其精准对应的所指对象,而是承认电影的内涵与外延具有多重、不固定甚至任意的指向。针对薛精华关于“寓言式意识形态批评”方面的阐述,张慧瑜指出,将寓言式批评引入科幻电影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二者的内在联系仍需进一步深化。他认为,本雅明作为现代寓言批评的重要源头,其理论与德国表现主义及早期科幻电影之间存在紧密关联。研究可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德国表现主义这一历史脉络出发,深入探讨本雅明理论与科幻电影创作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德国表现主义电影视觉手法在科幻电影中的传承与演变,可以揭示寓言式批评在科幻电影视觉语言层面的作用机制,从而夯实寓言式批评在科幻电影研究中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詹姆逊在科幻文学及电影研究中的成果,尤其是其政治无意识理论与寓言式批评方法,为解读科幻电影的深层意义提供了关键视角。换言之,科幻电影受社会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其叙事情节往往蕴含着政治无意识的内容。研究应借鉴詹姆逊的方法,剖析科幻电影叙事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寓意。例如,外星入侵题材可能隐喻当代社会中的阶级、种族或权力关系。此外,张慧瑜认为,研究对科幻电影空间的分类尚需进一步细化。科幻电影的空间具有多元形态与复杂功能,可分为物质与精神、现实与虚拟、公共与私人等类型。通过深入探讨这些空间类型在电影中的呈现方式、彼此关系及其对寓言表达的影响,以及它们与时间、人物元素的互动和历史演变规律,可以更全面地把握科幻电影的艺术特质与文化内涵。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寓言式批评的理论框架,还能显著提升其在科幻电影研究中的解释力与适用性。曲楠基于对科幻电影研究的深入洞察,认为该研究尝试运用寓言式解读方法来释放电影多元意义结构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创新性,值得肯定。然而,在处理寓言与现实关系时,该研究存在着过于二元对立的倾向,未能充分体现科幻寓言本身所具备的复杂二元统构特性。科幻寓言既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又超越了现实的局限,它与现实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曲楠进一步建议,该研究应当借鉴美国科幻作家与理论家詹姆斯·冈恩的相关观点,将科幻寓言置于现实场域内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讨论,打破简单的二元思维模式。例如,在分析经典科幻电影时,不应仅限于探讨寓言与现实的对应关系,而应更加关注电影如何通过虚构的寓言故事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反思或想象性重构。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世界设定往往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夸张或变形呈现,通过对这些设定的分析,可以深入挖掘电影创作者对现实的忧虑、期望以及对社会变革的思考。陈旭光从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的宏观视角出发,认为寓言式意识形态批评为理解科幻电影提供了一种新颖且深刻的视角。在当代学术语境中,他指出,这种批评方法如同一把钥匙,能够揭示电影如何通过寓言形式这一独特媒介,深刻反映社会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进一步指出,研究者在运用该方法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特别是要关注如何将寓言式意识形态批评与科幻电影的造型、空间构成等独特要素有机结合。他认为,科幻电影以其假定性和虚幻性为显著特征,这使得其寓言性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电影更加复杂和多元。例如,科幻电影中常见的极具想象力的场景设计和震撼的特效呈现等元素,都是构建寓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深入剖析这些元素如何与寓言式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框架相融合,从而更精准地理解电影的深层内涵与文化意义。
(二)科幻世界:假定性与断裂的抽象空间
科幻电影通过构建一个超越现实的未来景象,展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断裂的假定性空间,它在提供视听奇观震撼的同时也投射着现实世界的深刻寓言,基于此,薛精华从多个角度详细剖析了科幻世界中的假定性与断裂性。首先,薛精华指出科幻电影中的物理载体空间可以是大范围的星系乃至整个宇宙的重新书写,如《星际穿越》中对虫洞的描绘,也可以是小范围的失落世界,如《第九区》中隔离的外星难民区。这些大小系列空间设定脱离了现实世界的束缚,展现了一个充满异质性元素的新世界,同时也完成了物理空间对现实世界的抽象映射。其次,薛精华强调了科幻空间中冲突关系的重要性。她认为,物质空间与冲突关系的结合形成了科幻电影的寓言表达。例如《第九区》中人类与外星难民的隔离与冲突既是对种族隔离和难民危机的直接呈现,也是对现实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矛盾的隐喻,这些冲突关系通过空间的具象化表达使得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再者,薛精华还提到了科幻世界中的想象世界,这是一种可能性的世界,背后的哲学思想是“事物本来可以是不同于它们现在所呈现的样子”。她以安德烈·塔科夫斯基导演的电影《飞向太空》为例论述了科幻电影如何通过虚构的空间和规则来试图揭示人类潜意识和宇宙本质的可贵艺术探索。她认为,这种想象世界的构建不仅是对未知的探索,更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最后,薛精华总结了科幻空间的抽象性和寓言性。她认为,科幻空间通过对社会运行规律、经济状况、权力关系等的表现成为一种包含社会、文化等意义的抽象空间。这种空间虽然指向未来和虚拟情境,但其语境总是与当下社会高度相关,其往往通过夸张和扭曲的方式展现现实世界的矛盾并试图引发观众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正是这种假定性与断裂性使得科幻电影成为一种独特的寓言表达方式。针对薛精华在本模块的论述,邱章红提出,研究在深入探讨科幻电影的空间寓言时,还应适当关注科幻电影中的空间童话维度。从心理依存角度看,科幻电影对未来未知空间的想象具有抚慰功能,例如美好未来世界的描绘能够缓解现实压力。空间童话与空间寓言相互交织,丰富了科幻电影的空间内涵。此外,邱章红认为,研究还应关注科技与玄幻元素融合等科幻电影发展的未来趋势,并注意分析和阐释更多具前瞻性想象力的作品。例如,时空穿越、平行宇宙等概念以及超能力情节的出现,为寓言表达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形式。通过分析这些作品,可以进一步探讨科幻电影如何融合科技与玄幻元素,创造更具想象力和深度的寓言世界,以适应观众文化需求的变化。杜天笑认为,薛精华对科幻电影空间的研究在文化意义生成方面有深度,但对空间视觉性基础分析不足。她进一步指出科幻电影空间意象的文化意义构建常以视觉性想象为基,电影画面构图、色彩、光影营造的空间氛围和情感基调往往可以引发联想思考并衍生文化想象,例如经典科幻电影中的宇宙空间、外星地貌和未来城市景观等。杜天笑建议薛精华可以借鉴《异形》系列颜色对应主题的方式,加强对空间视觉性的直接描述,并通过深度分析颜色在电影中的叙事和寓言以揭示视觉元素背后的文化意义和象征价值。同时,还应多关注中国科幻电影或小说中的民族性意象,如《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体现出中国文化对人性、道德和宇宙秩序的理解等,通过引入中国元素可丰富研究内容、拓宽多元文化视野并有效促进中国科幻电影文化传播交流。
(三)寓言的历史性解读:科幻电影与世界社会的文本互涉
科幻电影既是视觉和想象的盛宴,亦是对世界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深刻寓言。薛精华通过对科幻电影的历时性解读,揭示出其如何与不同时期的世界社会环境相互交织,形成了丰富、复杂且深刻的文本互涉。首先,薛精华分析了冷战时期的科幻电影。她指出,这一时期的科幻电影充满了高政治的寓言,如其中的太空竞赛、外星侵略等主题都是对当时国局势的隐喻。她以《星球大战》为例深入分析了银河帝国与义军的二元对立,认为电影通过极端的环境和虚构的情境完成了寓言式表达,反映了人类对未知和恐惧的探索,同时也展现出现实世界的社会、军事和意识形态矛盾。其次,薛精华探讨了全球化时期的科幻电影。她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幻电影的主题逐渐从太空探索转向到生态危机、社会分层、数字监控等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她以《极乐空间》为例揭示出电影中富人与穷人的空间分隔不仅是对社会阶层固化的寓言式表达,也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她认为这些电影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极端呈现同样也引发了观众对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不平等的深刻思考。最后,薛精华关注了数字时代的科幻电影。她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科幻电影开始探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她以《流浪地球2》为例,论述了电影中对人工智能通过全景监控系统实现社会秩序维持、进而使权力无限膨胀并侵蚀人类自主性的科幻想象。她认为,这些电影通过对数字技术的极端想象反映出数字时代人类对未来生存状态的深刻担忧,同时也会引发观众对未来社会变革的深入思考。针对本部分的论述,陈旭光强调在不同的话语时期,社会文化语境发生着显著变化,这就要求在运用寓言式意识形态批评解读科幻电影时必须保持高度的反思和警惕,确保该批评方法能够与时俱进,并准确地解读出科幻电影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价值与影响。例如,在数字化、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科幻电影可能会通过新的寓言形式反映出诸如人工智能伦理、跨文化交流冲突等新的社会文化议题,寓言式意识形态批评需要适应这些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的分析框架,以更好地发挥其在解读科幻电影中的作用。庄维嘉认为,关于冷战时期科幻电影的隐喻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献,突破性的研究较为困难。因此,她建议将人工智能、气候问题等当代关键议题融入科幻电影的分析中,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同时,应深入探讨寓言与预言的关系,明确科幻寓言在科技蓝图、未来定义等方面的潜力和能力,并厘清它与科幻电影中其他主题寓言之间的区别,从而精准把握科幻寓言的本质特征,为科幻电影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庄维嘉进一步举例,建议分析科幻电影中人工智能寓言如何反映科技发展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与传统寓言在表达形式和意义内涵上的差异。通过这种研究方向的调整,科幻电影的寓言研究能够更加前沿、创新并具备可持续性。在电影文本分析方面,曲楠强调了揭示电影背后生产机制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幻电影的赞助方与权力结构、文化思潮和商业利益之间存在紧密关系,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电影的诸多方面。例如,冷战时期部分科幻电影受政府或军方资助,其外星入侵题材可能带有宣传意图。曲楠建议,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应深入挖掘科幻电影的背后故事,分析赞助方利益诉求与寓言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全面把握电影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此外,曲楠还建议关注导演风格、编剧手法、演员表演和特效运用等电影制作因素对寓言性的影响。他认为,不同导演对同一题材的处理因个人风格、文化背景和创作意图的不同而产生各异的寓言效果。通过对这些因素的细致分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科幻电影寓言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而避免简单化的解读。
二、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土地乡愁与伦理思考
刘婉瑶以《昨日的乡土:21世纪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土地与乡愁》为题,全面探讨了中国科幻电影中土地与乡愁主题,深入分析其背后的时空隐喻、伦理博弈及科玄之辩等复杂议题。与会专家在肯定选题的创新性与学术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研究中尚需完善的具体问题,并提出未来应重点关注的重要方向与关键议题。
(一) 制造乡愁:想象关于土地的“乌托邦”
在21世纪中国科幻电影中,乡愁情结往往将美好的、失落的美德放置于遥远且不可实现的乡土空间之上,使土地成为一种承载着特殊情感的意象。刘婉瑶认为,这种乡愁不同于简单的怀旧,它具有乌托邦化的强烈情感色彩,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后出现的文化和审美现象并与现代都市的兴起、工业的发展以及人际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例如在《宇宙探索编辑部》里,西南密林被赋予神秘奇幻的色彩,森林中的飞船、洞穴壁画等元素营造出一种奇幻的氛围,使土地景观带有陌生化的情感色彩,呈现出乌托邦化的效果;同样,《流浪地球》呈现了地球停转前的土地景观,以冰封状态展现的长城等元素体现了对土地的眷恋,尽管这种情感与科幻电影寻求惊异的原初目的形成矛盾,但却反映出人们在科幻想象中对失落的“黄金时代”或未进入现代化结构的理想社会的幻想。刘婉瑶认为,这种乡愁绝非简单的对往昔时光的怀念,其本质是在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这一宏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文化与审美现象,带有强烈的将过去乌托邦化的情感倾向。她进一步阐释道,这种乡愁的产生根源在于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对现实框架的认知与接受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差,进而促使人们在科幻电影的想象空间中寻求情感慰藉。同时,这也反映出中国科幻电影在对待科技发展这一议题上态度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是当代文化语境下人们内心世界在科幻电影艺术中的细腻呈现。
针对刘婉瑶的研究选题,张慧瑜认为,以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土地与乡愁为题,精准捕捉了中国科幻电影的独特特征,展现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为进一步深化研究,他建议拓展文本分析的广度,将《疯狂的外星人》《乡村教师》等更多具有代表性的电影文本纳入讨论,并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角,深入剖析中西科幻电影中乡愁内涵的差异及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根源。通过对比研究,可以揭示中国在想象科技未来时与土地、乡村紧密相连的独特文化逻辑,以及这种想象背后可能潜藏的保守主义倾向等复杂文化脉络。这种分析不仅为中国科幻电影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也有效拓展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为理解中国科幻电影的文化意涵与叙事特色开辟了新的路径。陈旭光认为,“科幻电影中的故土叙事”作为研究主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然而,该研究在论述过程中的案例选择较为单一,理论跨度较大且部分论述相对抽象,导致理论与论据之间的适配度不足,影响了研究的说服力。他建议增加案例的数量与多样性,例如挖掘不同风格、时期和地域的科幻电影案例,深入分析其中土地、乡愁与科学伦理等元素的呈现与演变。通过优化理论与案例的结合方式,研究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讨土地伦理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等核心议题,从而推动中国科幻电影研究迈向更高水平,为相关领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术资源与理论支持。
(二)土地是时空的隐喻:被放置在远方的土地
土地在科幻影片中承载着深刻的时空隐喻意义,这一意义的构建与表达贯穿于电影叙事与视觉呈现的多个层面。刘婉瑶从文化学与哲学的视角出发,以苏轼《赤壁赋》和《流浪地球2》等作品中对自然景观与时间关系的不同表述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科幻影像中自然景观时间观念的转变。她认为在科幻电影的语境下,土地景观不再仅仅是自然地理的实体,而是成为时间与空间交织的复杂符号。刘婉瑶以《宇宙探索编辑部》为例详细分析指出,中国科幻电影中土地景观的变化精准地映射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在时间维度上的冲突、错位与传承。如影片中主角从北京西站前往西南地区的旅程,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位移,亦在叙事层面上体现了土地与城市之间从相对到对立的关系演变,使得土地在影片中逐渐被塑造为一个与现实存在心理距离的、充满想象性的乌托邦空间,蕴含着深刻的伦理批判意义。她进一步认为,土地在科幻电影中的时空隐喻通过景观层面的自然转化、时空一体化的叙事构建以及富有情感性的想象结构等多个维度得以系统呈现,充分反映了中国科幻电影在时空观念表达上的独特艺术追求与文化思考。庄维嘉对刘婉瑶提出的“土地是时空的隐喻”这一核心观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极具学术价值。同时,她建议在后续工作中进一步梳理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西方关于时间与空间哲学观念的演变历程。例如,在中国农业社会中,基于农耕生产方式形成的独特循环时间观和乡土空间观,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土地的认知与情感依附;工业社会的兴起则带来了线性时间观和城市化空间扩张,不仅显著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重塑了时间与空间的感知模式;而进入量子计算时代,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变得更加抽象和多元,这一系列变化深刻影响了乡愁的内涵与外延,并重塑了科幻电影中土地意象的表达形式与文化意义。曲楠认为,该研究展现了宏大的理论架构和丰富的知识储备,但在内容整合上仍存在一定问题,具体表现为内容驳杂、跨度较大且部分论述不够深入。尤其是在阐述时空相关概念时,如乡愁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演变,这一主题极为复杂,涉及社会、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其背后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建构机制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剖析。他指出,研究过程中应避免对既有理论的简单引用,以免稀释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而应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际案例之间的内在联系,强化理论的阐释力。同时,在学术术语的使用上需更加严谨,例如乌托邦、异托邦、恶托邦等概念,需明确区分其内涵与外延,避免混淆。通过这些改进,可以有效提升研究的质量与学术价值,使其更具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
(三)景观的情感化:乡愁背后的伦理博弈
乡愁背后隐匿着复杂且深刻的伦理博弈关系,这一关系在电影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以及主题表达等方面均有显著体现。刘婉瑶以《三峡好人》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解读,指出其中三峡工程带来的城市淹没等情节深刻象征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追求效率的发展模式,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与压抑以及由此导致的部分群体文化特性的消逝,这种土地景观的剧烈变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体现出市场化逻辑与乡土文化中人文关怀的强烈冲突。同时,刘婉瑶在研究《宇宙探索编辑部》等影片时着重强调,科幻电影在展现科学与土地关系的过程中巧妙地融入了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通过影片中不同角色的性格对比、行为选择以及价值取向的差异(如秦彩蓉与唐志军在对待外星人存在、对待科学探索等问题上的分歧),生动地展现了理性与理想主义两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与博弈。她系统地总结认为,中国科幻电影通过对乡愁元素的深入挖掘与呈现深刻揭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文与科学两种伦理价值体系的对立与融合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同理想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异与张力,这无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核心难题在电影艺术领域的集中呈现与深度反思。在评议环节,与会专家一致肯定了乡愁作为一种情感结构,其生成深受社会发展背景的影响,并与城市化建设等社会进程密切相关。曲楠认为,研究选取《三峡好人》作为案例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影片中展现的乡愁与生态美学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影片通过生态景观的变化以及人物对失落家园的追寻,揭示了乡愁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宏观脉络中的复杂体现,深刻反映了大规模建设背景下个体情感体验与文化记忆的变迁。同时,曲楠也指出,对影片中UFO场景等电影语言形式的分析还需更加深入和多元。该场景不应仅被视为简单的科幻元素呈现,而应从个体在纪念碑式建筑或废墟情境中的生存状态、身份认同与文化记忆传承等角度展开解读。通过借鉴城市文化研究、建筑批评、文化记忆理论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丰富对这一场景的理解,并深化对科幻电影的全面分析。此外,陈旭光、张慧瑜、庄维嘉等专家认为,应更加精准地界定科幻电影的研究范围。对于《三峡好人》这类处于科幻边缘或具有争议性的电影案例,需要从叙事逻辑、视觉元素、主题表达等多个维度综合考量,深入探讨其是否符合科幻电影的典型特征。这种界定不仅有助于为研究框架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也能为案例选择提供合理支撑,进一步完善整体研究的学术严谨性和系统性。
(四)科玄之辩背后的价值选择:中国现代化语境下“科学”的意识形态与寻不到的伦理
作为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渊源和广泛文化影响的议题,科玄之辩在中国科幻电影的语境中深刻影响着电影的价值取向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核心矛盾。刘婉瑶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系统梳理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科玄之辩论争在不同时期科幻作品中的演变与呈现:在晚清科幻小说中,梁启超等人的作品已经开始体现出对科学与社会变革关系的初步思考,强调科幻小说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则更加注重将科学作为导引理性的重要工具以实现对民众的理性启蒙。刘婉瑶进一步指出,在当代中国科幻电影中,如《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所展现的人机关系深刻地体现了绝对理性与科学发展质疑和人文思考压抑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深入分析,她认为,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经历“压缩现代性”的特殊历史时期,科幻电影一方面反映出对科技理性的一定保留态度,试图在科技发展的浪潮中寻找人文精神的栖息之所;另一方面,在伦理重建这一关键问题上却面临诸多困境且难以在回望乡土的姿态中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最后她概括性地总结指出,这一系列现象充分体现了中国科幻电影在时代洪流中的价值困惑与艰难探索,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科技与人文、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张慧瑜认为,研究中涉及的每个视角都具有独立深入研究的潜力,每一角度均可拓展为一篇具有深度的学术论文。然而,他指出,目前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连贯性和内在呼应性略显不足。若能紧密围绕核心问题——如中国科幻电影为何呈现“向内转”趋势以及土地想象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系统性探究,将显著提升研究的整体性与深度。在研究过程中,他建议更加注重从科幻电影自身的发展脉络出发,避免过度延伸至与科幻电影关联性较弱的领域(如乡土文学),以确保研究焦点的集中性与路径的合理性。同时,研究可进一步强化对电影文本的细致解读,深入挖掘情节与画面背后的文化密码,从而增强研究的针对性与学术价值。这种调整不仅有助于丰富中国科幻电影的理论建构,还将为相关领域提供更具深度与创新性的学术贡献。邵将提醒刘婉瑶在本部分的写作中应高度重视行文措辞与语气的严谨性。尤其在涉及中国科幻电影发展历程、特点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时,务必确保表述的客观性与准确性,避免因措辞不当而传递出过于悲观或带有偏见性的观点,确保研究内容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在体现学术创新的同时又能符合国家主流文化发展的整体导向。陈旭光指出,该研究涉及科学与乡土现代性、回望乡愁的伦理问题等多个复杂领域,并与生态美学具有一定关联。然而,在论述过程中,这种关联的阐释尚不够清晰明确,影响了研究的系统性和逻辑严密性。因此,他建议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科幻电影史的挖掘,广泛收集并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科幻电影案例,深入探讨土地、乡愁、科学伦理等元素的表现形式及其演变过程,以强化理论与案例之间的有机结合。在理论运用方面,他认为应更加注重理论的适用性与创新性,避免简单套用已有理论,而应结合中国科幻电影的实际情况开展理论创新与精准阐释,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结语
科幻电影通过空间建构与历史语境的互动,深刻反映了社会文化转型的复杂性。本次沙龙的分享与研讨深入探讨了寓言式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揭示了科幻电影如何通过视觉语言和叙事结构反映现实世界的社会矛盾,突出其在文化批评中的独特地位和理论价值。此外,不同时期的科幻电影中的时空观念及其哲学意涵,揭示了土地作为时空隐喻在叙事中的多重功能。这一功能不仅承载了中国文化对乡土的深厚依恋,还凸显了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伦理博弈。通过对土地与乡愁主题的探索,中国科幻电影展现了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文化视角与社会关怀。随着技术发展与观众需求的不断变化,中国科幻电影将在文化记忆与未来愿景的交织中,持续探索新的叙事可能性。这将进一步深化中国科幻电影的文化表达,并为全球科幻电影的多样化发展提供独特的视角和创意。
【作者简介】

蒋佳音(1997— ) ,女,江苏徐州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23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理论与批评、影视文化、中国电影史

邵将 ( 1990— ) ,男,山东聊城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理论与批评、网络与新媒体。

陈旭光( 1965— ) ,男,浙江东阳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 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影视文化、影视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