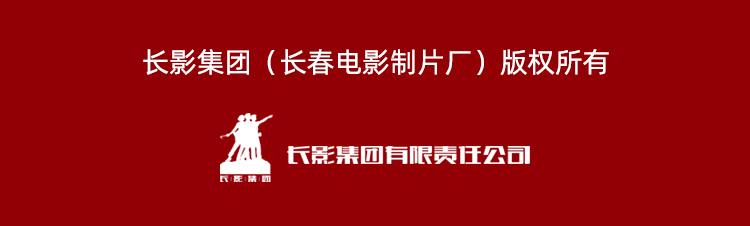【开栏语】
今年是长影成立80周年。80载光影流转,长影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不仅孕育了《白毛女》《董存瑞》《创业》等影响几代人的经典影片,更沉淀了一代代电影人对艺术的执着、对时代的热忱。
为此,我们特别推出专栏《长影80周年·光影记忆》,在艺术家们的回忆里品味热爱与信念的甘醇,探寻长影80年的成长故事。
本期,我们首先推出专栏第一篇——《总编室,我放飞梦想的地方》,带您走进长影“一剧之本”的诞生地,看那些藏在剧本背后的热血与坚守。
该文作者王霆钧老师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等多个协会会员,1975年进入长影工作,曾任长影文学部主任、艺术处处长,在长影深耕34年,亲历了中国电影的转型与发展,更与无数长影前辈共事,见证了太多不为人知的创作往事。
在本期文章里,你会看到长影如何培养“懂电影的编辑”;跟着老编辑走南闯北组稿,在田间地头寻找创作灵感;甚至要深入煤矿、油田体验生活,只为让剧本里的每一个字都带着生活的温度。文中有太多让人动容的细节,这些细节,藏着长影的“传家宝”。
总编室,我放飞梦想的地方
王霆钧
一
2025年10月1日,长影迎来80华诞。
多少年来,长影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她曾被称为新中国电影摇篮,为中国电影界输送了许多艺术、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她也被称为艺术圣殿,出品过多部至今还人们津津乐道的优秀影片。我曾不止一次听说,“我是看着长影的影片长大的”。长影的许多经典影片影响了不止一两代人三观的形成。
我为长影骄傲,也为曾是长影的一员自豪。
总编室初创于1955年,当时叫编辑处,处长是《红旗谱》编剧胡苏。后来更名为总编室,胡苏任副厂长主管剧本工作之后,总编室主任由《智取华山》的编剧纪叶担任;田野、韦连城、马新福,荏荪、刘朝荣担任过副主任。我记得,这时期的老编辑有南吕、刘灵、徐世彦、赵琪、符生、孟宪英、徐明、侯野萍、白帆、张希至、李威伦、高鸿鹄、黄昧鲁、张育慧、许贻来、陈曼倩、郑会立、石城、李方钧、惠屹等人。七十年代初期,分过来三个大学生,他们是吉林大学的金德顺,东北师大吕文玉和李超。前二人后来也担任了副主任。在《吉林文艺》担任诗歌编辑,推出我的处女作组诗《硕果累累》的任彦芳老师也曾是总编室的编辑。不过,他们已经调出长影。
长影是三大电影厂年产量最多的一家,每年都是二十部上下。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要保证影片生产,至少要准备五十部左右供厂里挑选。因此,抓好剧本是厂里对总编室最大的期望,也是编辑最重要工作。

新中国电影剧作家的摇篮——小白楼
为了解决编辑队伍青黄不接问题,适应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厂里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陆续从大学、工厂、知青、复员转业军人和文化团体,招收了文学爱好者二十多人,如赵葆华、曹积三、常安、张万晨、王兴东、王浙滨、贺恒祥、姜淑云、高艳如、王驰涛、徐恩志、贾力先、刘伯军等;也有从厂里其他部门转过来的如王晓莲、高为人、庞鹰等;后来又有梁恩泽、李荣霞、韩志君、赵保康、黄海刚、李秋燕、戴人坚、赵韫颖、侯若萱、王小妮、李东东、谢燕南、冷杉、徐远翔、赵俊梅、赵鸿雁、钟研、王天明等陆续调入。也有调进来又调出的,如徐恩志、庞鹰、高艳茹、马新福、王小妮、李秋燕、戴人坚、徐远翔、冷杉、庞鹰、钟研、王天明、赵韫颖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被错划为右派的宋鷁、牛有山二位老编辑回到室里,老编辑陆玉英也回归室里。不过,陆玉英和牛有山很快就退休了。
在韦连城主任担任剧本厂长之后,梁恩泽、南吕分别担任过总编室主任。李荣霞担任过支部书记。老编辑孟宪英、张希至、李威伦、高鸿鹄、黄昧鲁、许贻来、陈曼倩、石城等人相继调出,或到外厂或到外单位工作。
总编室下设办公室、编辑、编剧和评论三个大组。编辑组又分为两部分,一是组稿组,二是来稿组。厂里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群众来稿,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不可忽视。来稿组收看群众来稿,领导要求每稿必看,看后回信。组稿组分江南片、江北片和华北片、东北片四个小组。纪叶老师创办并担任主编在全国广有影响的《电影文学》复刊之后的编辑部也设在总编室。后来《电影画报》复刊更名《电影世界》,厂里把《电影文学》划出去,成立统管两个期刊的办公室。赵子明和黄昧鲁担任领导。在评论组撤销后,高鸿鹄担任了《电影文学》总编。担任译制片剧本翻译如尹广文、刘迟、胡伯胤等也曾在这里,后分离出去。
《上甘岭》的编剧林杉曾是副厂长,尚未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桥》和《赵一曼》的编剧于敏先生是编剧组成员,长期在鞍钢深入生活,连家也搬到那里,有重要事才回厂来。后来,林杉和于敏都调到中国影协工作,前者担任《大众电影》主编、后者担任《电影艺术》主编。著名编剧王震之、沈默君曾在编剧组工作过。记得我初到总编室时,编剧组编剧有张天民、郑荃、房有良、肖尹宪、周新德、李玲修。后来张笑天、王兴东、王浙滨、顾笑言、韩志君、盛嫚姝、杜丽鹃等也调入编剧组。张笑天、韩志君先后担任过厂里主管剧本的副厂长。张笑天后来调到省作家协会和省文联任领导工作。
我开始到总编室,曾在来稿组看一段外稿,不久分到组稿组,先在华北片后又到东北片。东北这一片的领导人就是后来因参与《保密局的枪声》编剧而名声大震的金德顺。
改革开放之后,编辑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过各厂文学部主任呼吁,电影局同意编辑可上字幕,列在副导演之后。刘灵同志成为长影第一个上字幕的责任编辑。
二
虽然同为编辑,不同于戏剧剧本编辑、小说编辑,电影剧本编辑有特殊性。电影的基本元素是镜头,什么是镜头,如何在电影剧本中体现镜头感,让导演拿到手里就能进行分镜头创作,进而投入拍摄,这可不是大学毕了业进入电影行就能够胜任的工作。即使你是电影文学专业毕业,恐怕也要在实践中磨砺几年才能适应这份工作。
我刚当剧本编辑不知道什么是电影剧本,也不知道如何判断一部电影剧本优劣。室领导自然明白如何培养出一个够格的编辑。于是,我们边工作边学习,边学习边工作,在室领导精心呵护下,在老同志精心带领下,我们陆续成长起来。
室领导为培养新人采用哪些措施呢?
其一,派到摄制组担任一、二部戏的场记。
我到总编室报到,主任就告诉我,要当好一个电影剧本编辑必须了解电影摄制过程,了解什么是镜头。于是我被派到原《创业》剧组正在筹拍的《希望》;王浙滨到《金光大道》剧组。跟我同时到总编室的聂凤伦到《长空雄鹰》剧组;唐兵到《占领颂》剧组,这二人后来就留在摄制组,没再回到总编室。王兴东曾到《保密局的枪声》剧组。我在剧组两个月,只是影片筹备阶段,剧组结束筹备阶段返厂,我按要求回到总编室。我虽然下到剧组了,但影片没有开机,还不算下组。刚好正在摄影棚里拍摄的《黄河少年》,场记崔东升感冒休息,剧组需要场记,我又被安排过去代场记,导演是陆建华和李光惠,后者也是摄影师。导演和摄影研究剧本时,委托助理和我拍摄一个道具的空镜头。助理调整好焦点,让我掌握时间喊停。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喊停,是助理觉得应该停了自己停的。他哪里知道我这个场记初来乍到对电影拍摄完全外行呢。不管怎样,我知道了什么是镜头,而且在拍摄一位抗日游击队队员进一个小院时,副导演让我穿上游击队军装,在门口晃了一下,当了一把活动背景。影片完成后,我在银幕上看见了自己,在镜头深处人影模糊,不特别注意即使熟识我也看不出是谁。一周之后,我回到总编室做剧本编辑工作,再也没有涉足摄制组。
其二,以老带新,外出组稿。
刚来做编辑,领导不敢单独放飞,往往都由老编辑领着出去,了解编辑工作程序,知道如何做编辑工作。组稿编辑首先要建立剧本作者队伍。一些能写剧本的作者往往都有老编辑联系,新编辑不能控墙角,要自己去寻找新作者。到哪儿去找作者,又如何确定选题。这是编辑基本功。我们跟着老编辑下去就是要了解如何寻找作者,如何确定选题。我曾跟着老编辑徐世彦、赵琪、孟献英、李晓峰、侯野萍、金德顺、吕文玉到南京、合肥、涡阳、沈阳等地组稿,也曾在领导安排下和同时当编辑的贺恒祥一起到山西组稿。如果有导演外出组稿,在室领导安排下也可以随行。在《金光大道》剧组实习的电影学院教员王运辉曾去河北组稿,领着我到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组稿多日。
以老带新不仅在组稿组,编剧组也是如此。
《金光大道》是北京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他的《艳阳天》已经由长影搬上银幕。《金光大道》还在创作中,就被长影“号”上了。所以,小说还没出版,厂里的改编工作已经开始。第一、二部陆续上映,反响热烈。厂里在组织第三部剧本改编时,总编室领导派我加入该剧本创作组,学习剧本改编。我就跟着肖尹宪老师,还有导演孙羽和他的助手吕绍连、罗渝中,在位于长春远郊的左家镇吉林省农业科研所的招待所里开始探讨剧本的改编。
记得那是秋末冬初,天有些冷,招待所的二层楼房,除了我们别无他人。小说还没出版,由厂里打印出来装订成厚厚的几大本。我们每天都集中到一间屋里,读小说,谈剧本,然后研究如何改编。每天早饭后集中,先是一章一章地读小说,然后孙羽老师一场一场地讲戏,有人物有环境有对话。在这个创作组中,肖尹宪曾经参加《金光大道》前二集的改编,对其中一脉相承的人物是熟悉的。吕绍连和罗喻中都是电影学院毕业生,前者学的是导演,后者学的是表演,已经在长影工作几年,有相当的创作经验,所以在研究改编的时候,时有争论,各抒己见。只有我一个人默默地听,迅速地记录着他们的发言,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根据讨论帮助肖尹宪整理成剧本。大约半个多月的工夫,改编本完成,打印若干份征求意见。我们曾为这到北京,听取原著作者浩然的意见。那时的浩然才四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给我的感觉好像已经五十多岁的样子。但他精神很好,十分健谈。他对剧本谈了什么意见我已经印象模糊,但他说的,每天坚持写三千字的事让我牢记至今。他这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创作态度,使我受益匪浅。
《金光大道》剧本完成之后,四人帮垮台,厂里调整题材规划,下部下马没有投拍,这也是《金光大道》影片只有上集、中集两部而没有下集的原因。
唐山大地震之后,厂里派出人去深入生活,准备写表现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的剧本,肖尹宪带上我又到废墟遍地的唐山开滦煤矿生活多日,肖尹宪的剧本《特别能战斗》写出来了也没投拍。
其三,送到电影学院深造学习。
电影学院恢复招生之后,除对在校学生进行电影艺术教育之外,还开办培训班,招收各电影机构在职有学习意愿的学生进行培训。王浙滨、王兴东、赵葆华、贺恒祥、刘伯军都曾前去进修。电影学院成立高级班培养研究生,韩志君曾去学习。1980年,电影学院举办编剧培训班,厂里选派了我和王晓莲、侯若萱三个编辑前去学习。当时学院在远郊朱辛庄,原是北京农业大学校址。后来影响了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张军钊、田壮壮等人正在校内学习。为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写作剧本的编剧张子良在我们班里。我们在那儿进行了一个学年两个学期的学习,由电影学院老师授课,根据需要也从学院外请在电影艺术和文艺理论方面有造诣的名人讲课。观摩国内外优秀影片。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但极左思想还有一定势力,观摩国外影片受限,自然也影响了教学。不过这段学习对我成长还是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四,参加各种电影艺术研讨活动。
厂里经常举办电影艺术研讨会活动,从北京调来外厂的国外的优秀影片供厂里艺术干部观摩。从厂长到摄制组,凡是艺术干部没有特殊情况一律参加。总编室的人是必须参加的。看完影片还要讨论,看别人之长,找自己不足。室领导要求我们新编辑不能当听众,光是听老编辑说长论短,也要积极发言,勇敢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使发言有针对性,有自己的想法,领导要求我们写成稿子。那时,除几家大电影厂有电影期刊之外,有些省电影公司都有电影评论刊物,比如黑龙江电影公司的《电影百花》,贵州省电影公司的《电影评介》等。我的几篇稿子就发表在这些刊物上。
八十年代,我加入了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成立之后,我即是会员。这些组织都时常举办电影观摩和学术交流活动。有的时候,不仅我们编辑赴会,我们还会约社会的一些电影编剧参加。我曾经以《小巷总理》编剧的名义参加过中国影协、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组织的中日电影文学交流活动。在日本,放映了影片,然后同日本剧作家一起探讨,听日本同行对中国电影剧本的见解,受益匪浅。

1960年2月,长影举办第1届剧本业余作者讲习班结业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剧本业余作者在摄影棚里合影
《电影文学》为团结广大剧作家也常举办笔会,办过乐山笔会、贵州花溪笔会、长白山笔会等。全国有影响的剧作家、小说作家均可约来参加。我参加过1982年四川乐山笔会。乐山是大文豪郭沫若故乡,离宋代文豪三苏家乡不远。在那儿办笔会极有号召力,应约到会的名人很多,比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编剧,山西作家马烽;《葡萄熟了的时候》编剧,山西作家孙谦;《知音》编剧,山西作家华而实;《大渡河》编剧,黑龙江作家鲁琪;《笑逐颜开》编剧,黑龙江编剧丛深;长篇小说《风雷》作者,安徽作家陈登科;《济南战役》编剧,济南军区创作组的李虹宇;《红牡丹》编剧,山东省作家阎丰乐;《边城风雪》作者,内蒙作家张长弓,《丫丫》编剧,安徽作家刘克;《青年刘伯承》编剧,江西作家毕必成;《夜幕下的哈尔滨》作者,辽宁作家陈屿;《丹凤朝阳》编剧,吉林作家鄂华等人。参加会议的还有由长影调到峨影的22大明星之一的李亚林、长影主管剧本工作的副厂长纪叶、导演于彦夫、编剧张天民、张笑天等。会议在成都报到,然后坐大巴车游都江堰、青城山、峨眉山、三苏祠,还在途中几个先进的农村和企业采风。最后到乐山停下开会。时任《电影文学》主编高鸿鹄主持会议,期间游览了乐山大佛和大渡河等处名胜。《大渡河》的编剧鲁琪很有感触,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到大渡河来。会议结束之后集体到重庆,坐船顺流而下,过三峡到宜昌,最后在武汉解散。我参加笔会承担为大会服务的任务,开会时作会议记录,会前会后跑前跑后地帮助安排行程和食宿诸事。
其五,倡导深入生活。
总编室领导非常开明,不仅提倡编剧要深入生活,也倡导编辑深入生活。室领导认为,编辑不熟悉所组剧本的生活,剧本也未必能够扶持好。要求编辑出去组稿,不到二个月,不经允许不准回厂。外出组稿的期间,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到风景名胜地参观游览,也不反对。宽容的室领导认为那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工作期间,一出去就是二个月以上,到省、市的作家协会、文联、文化局、出版社等部门,去找作家和编剧们了解他们的写作信息,有电影剧本看剧本,没有剧本看他们的小说或者舞台剧本。做完这些后,我就到生活中去。我的一些小说和散文的部分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上述这些活动,对提高编辑的工作能力有极大帮助。
总编室老编辑刘灵曾回忆道:
1975年7月25日,毛主席就影片《创业》做出批示,敲响了四人帮垮台的丧钟,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件。不久,新华社派来了一位记者来长影各个部门采访,也到总编室来了解情况。几个月后,这位记者在《大参考》(内参)中发表了关于长影总编辑室的专题报道。文中除了谈到总编辑室人员组成、一般编辑工作外,特别写到长影的编辑们去全国各地邀请作者组织稿本的情况,文中写了一些制片厂的编辑在发现新作品登门拜访作者约稿的时候,作者常会说:“啊,长影厂的编辑已经来找过我了,我们约定了。”当然,长影总编辑室的编辑们,谁也没想到会得到新华社记者如此的赞誉。

1980年代,长影总编室外稿组的编辑们在审阅作者来稿
长影总编室得到了新华社记者的赞誉,那是前辈各位编辑努力工作取得的成绩。我能够成为他们的一员,也感到非常自豪。长影剧本编辑在全国电影剧作者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凝聚了总编室几任领导的心血。
那时的总编室还有工会,是厂工会的下属机构。每当哪个同志有了困难,工会发挥作用,积极帮助职工解决困难。我的婚事就得到了室领导和工会的极大关心。几十年过去,每每想起当初室领导和室工会和全体同志积极帮忙找房子,布置婚房和参加婚礼的情景都让我心里热浪翻滚。
三
电影厂体制几经改革,编辑机构也几经变化。九十年代初期,总编室缩编成文学部、不久又变成策划部。一些老编辑分流出去,增加了专职事务员周双秋、新编辑王志愿、尹江春调入。在策划部期间,一度成立两个部,厂销售部也纳入其中,我和曹积三分别担任两个部主任工作,归宫喜斌领导。此时,大学毕业生游伟来工作。
在全国性电影业务交流活动中,有一项是编辑部主任联席会议,每年一次,轮流做庄。在总编室缩编改为文学部之后,我曾担任过将近十年的主任工作,参加过多次会议。在会上,各厂交流题材。进入九十年代后,电影创作出现滑坡现象,主任们忧心忡忡,担心各厂体制改革会冲击编辑部门。这些担心很快变成现实。各个电影厂的编辑部门不复存在,剧本编辑分流。不管编辑部门如何变化,编辑们都在不同的部门发挥自己的作用。
经过多年学习和历练,总编室的编剧和编辑的业务水平都得到了提高。编剧组的编剧们每人都取得非凡的成就,电影剧本在国内外获得多个奖。编辑组的编辑们也不示弱,在他们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在创作上也多有亮点。老编辑刘灵、徐世彦、张育慧、金德顺、李超;新编辑赵葆华、赵韫颖、贺恒祥、赵俊梅,李冬冬、曹积三等都有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精彩亮相。离开编辑队伍转行导演的金德顺、冷杉、黄海刚在影视导演上成就非凡。编导一肩挑的韩志君更是把影视做得风生水起佳作连连。长影体制改革后,身为集团副总经理的韩志君担起了长影第一影视公司总经理重任,在电影低迷产量滑坡的年代,克服重重困难拍摄影视剧,成就了长影集团产量的半壁江山。高鸿鹄、赵葆华、王兴东、王浙滨、张万晨、李玲修等调离长影之后,也都在各自单位做得非常出色。王兴东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电影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王浙滨转行制片后,在制片和编剧两个行业一路风光;赵葆华的电影剧本接连获奖,担任了全国电影审委会委员;高鸿鹄担任过广西电影厂厂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郑会立转行导演拍电影,后南下组建了深圳电影制片厂。赵韫颖先是到省广电局电影处分管电影,后调到上海戏剧学院当上了教授。
我从到长影工作直到退休离开岗位,在这里工作了34个年头。初来时,我只是一个有着作家梦的文学青年,时至今日,已有十余部影视剧本搬上银幕或拍成电视剧,另有几部电影剧本发表在期刊杂志上;有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等多部书出版,仅写长影的出版物就有八本。长影让我美梦成真。可以说,如果不是在长影这样的环境,我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长影历来有培养人才的传统。早在东影时就曾办过电影学校。撤退到兴山之后,为了适应生产需要,厂里办过四期训练班,围绕影片生产和发行培训。学员经过学习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之后就安排到生产当中,让他们在实践中继续学习。1958年,厂里曾经办过非常正规的电影学院,面向全国招生。遗憾的是后来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学院下马,将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转到东北师大,在那里完成学业。后来在影视创作上成绩突出的几位编剧如顾笑言、肖尹宪、周新德、赵万捷和郑会立都是长春电影学院的学生。
长影如同一座艺术大学。电影是综合艺术,文学、表演、导演、摄影、美术、录音、服装、道具、化装、照明、字幕、作曲、歌唱、器乐演奏等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人才应有尽有。仅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泽东主席关于文艺讲话的人就有十多位。一些老艺术家,他们或来自延安鲁艺、或来自延安抗大文工团和革命根据地的演出团体,也有参加过东影初创的老艺术家。他们都是取得很大艺术成就的大艺术家,但他们从来都是谦逊的,没有在我这个小字辈面前高高在上。我至今记得苏里导演到我十二平方米的斗室里谈剧本。浦克到我的单身宿舍里去约我为他们庆祝重大节日写朗诵诗的情景。按他们的年龄和身份,完全可以打一个电话让我过去谈。他们没有。他们亲切和蔼的作风让我深受感动。
长影是我放飞理想的地方!也是我的同仁们放飞理想的地方!
感恩长影!每一位前辈都是我的老师。
我在长影获益多多。
感恩总编室每一位助我成长的前辈!
(2025年6月26日改)
【作者简介】
王霆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1968年应征入伍,1972年在吉林大学中文系。1975年到长影工作。曾任长影文学部主任、艺术处处长兼吉林省电影家协会秘书长。现已退休。
写作电影剧本并拍成影片的有《小巷总理》(与肖尹宪合作),《关东民谣》(与高满堂合作),《黑旗特使》(与宁宣成、符生合作),《怪侠》;电视电影《少奇专列》(与黄亚洲合作),《特别通行证》等十部;电影剧本《东西屋南北炕》获夏衍杯电影创意剧本奖。电影《小巷总理》获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和长春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电影《关东民谣》获得国家神农杯银奖;电视电影《少奇专列》获得首届电视电影百合奖一等奖;长篇电视剧《月色无言》获得天津市长篇电视剧一等奖、飞天奖提名。电影剧本《东方欲晓》(与李前宽合作)入围阳翰笙剧本奖。
出版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寻回自己》、中篇小说集《美人痣》《秘密寻查》,其中《知羞草》获《长春日报》连载小说二等奖;散文集《王霆钧散文》《永远的电影》《长影的故事》《光影花魂》和长篇报告文学《画里画外》(与王乙涵合作)、《超越》(与李景田合作)、《大师小传》(和王乙涵合作)、整理了韩蓉长篇回忆录《情系黑精灵》、长篇纪实《长影往事三部曲》等。散文《三山行》获首届徐霞客游记文学大奖;散文《多一些微笑吧》获优秀散文奖,收入《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和《中学语文课本课外读物》;个别篇目被收进大学参考书中。曾获得长春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并获长春市创作成就奖。